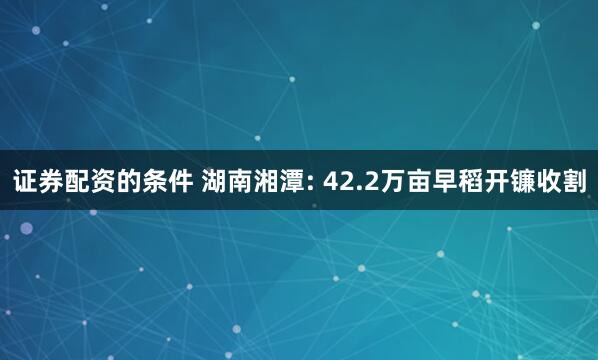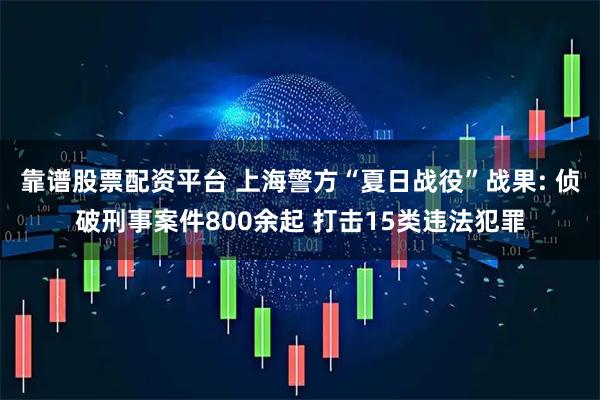潮新闻客户端谢邦君杠杆配资公司

请输入图片描述
风,带着灵江水的湿冷与咸腥,从远处吹来,掠过石鼓空寂的码头。站在荒草蔓生的旧埠头,闭上眼,仿佛就能穿透岁月的尘烟,看见那一艘艘黝黑的长船,借着潮汐的伟力,溯流至此。船身吃水深深,船舱里压着的,是沉甸甸的四方货物,是商贾奔波的生计,是西乡人家灶膛里的一点暖意。它们从历史深处驶来,穿过眼前这弥漫的雾气与时光的尘埃。
切莫小瞧了这方寸之地。石鼓渡头,曾是灵江上游小舟常年能抵的咽喉。大水潮涌,能漫过村后方始丰溪中那块早已炸毁的江心礁岩;小水时节,船影便徘徊在石鼓渡下游。潮来时,江面最阔处可达二百米,平日亦在百米上下。江宽水深,水流平缓,波光安稳,正是千帆汇聚、万货流转的天然良港。这里是始丰溪与永安溪两条水路的交汇之所,更是通达金丽、绍杭两大陆路的转捩之点。水路陆路,在此纠缠、接力、奔赴远方。得天独厚的地理,早早将石鼓催生为西乡辐辏之地的大集散点。
靠潮水推涌的长船,载着下游各地出产或转运的物资,顺潮汛而至,每每枯水季,或者寒天,当长船上的船帮已吃不消下水拉纤时,长船即无力继续溯上,终泊于此。沉重的麻袋、木箱、竹篓从船上卸下,由码头劳力人的脊梁扛起,转交到另一群铁打的肩膀——挑脚担夫们的手中。这些货物,连同本地的山珍土产,便化作一副副扁担下的重负。他们沿着杭台古驿道,一步一颤,将生活与远方挑向天台方向。再过关岭,下剡溪,汇入曹娥江水系,最终抵达绍、杭,乃至更辽阔的世界。西乡这片土地,因此成了台州眺望外界的一道不可或缺的生命通道。
当初西乡,能让家人吃饱饭的营生无不与这一溪一道带来的物流行业相关。典型如拙文《那溪那船那人》、《江上的父亲》介绍的长船老大与船帮(水手),与这古驿道上,其它篇章各异的物流形式,共同交织成一曲生计的交响:
一、步履刻痕:挑脚担夫
清一色矮小精悍的精壮汉子,皮肤被日头与汗水浸染成古铜,或黑或灰的粗布短褂紧贴脊梁。箬帽遮阳,草鞋踏泥,一条吸饱汗水的毛巾斜搭肩头。手中一根实木短拄,拄脚箍着铁圈,是换肩时的支点,是歇脚片刻的依靠。每人一担,百廿斤分量,是生活的秤砣。货物成批,路远人稀,绿壳(土匪)出没的阴影如影随形,故而他们必得结伙而行。从临海城垣,或石鼓码头接了船货,日行五六十里。有“天台担”,百里路途指向天台县城的溪头埠头,中间常在仙人村歇脚,回头再挑上天台运往临海的“回头货”;有“河头担”,当日直抵大石洋那片开阔地,再由当地挑夫散入深山褶皱。
记忆深处,多次在八叠岭目睹那行进的队列。上岭时,前担绳短,后担绳长,扁担俱压左肩,短拄扛在右肩,拄脚顶着扁担着肩的后方,右手搭在拄头使力,将部分负重分至右肩。
排头掌控前行的节奏,一步踏出,十几条汉子身体齐向左倾,旋即右斜,“嗨啊”、“虾啊”的整齐划一的号子声此起彼伏,头颅同步一翘一颌,如一波涌动的黑色浪潮,在青石板上起伏翻滚,煞是雄浑凝重。
乏了,排头短拄“笃”地一顿,铁箍敲击石板,脆响如令。他迅速将拄头插进扁担前部的绳结,撑住前担,后担落地,侧身卸肩。其余人如应声之弦,依次各慢半拍,依样画葫芦,整个队伍动作行云流水,丝般顺滑,宛如一列精密的骨牌次第安歇。
分把钟光景,喘息未定,排头复又起肩,队伍便在铁箍与石板的交响中再次蠕动前行。问过父亲,缘何不多歇片刻?答曰:“歇久了,筋骨就懒了,后头的路便没了气力。”这分毫必争的喘息,是刻在骨子里的生存智慧。
那些黝黑的肩膀,除操着天台的腔调、大石的乡音的班头外,多是八叠周遭的乡党。班头是各方共同信赖的挑脚担头领。由乡绅、保长对货主担保经营,然后再重托给班头。再由班头挑选合格信得过的挑脚担夫。这是卖力气的营生,挑脚担夫的收入略强过长年(长工),比不得船帮的利厚,却也养活了一方烟火。

二、蹄声如雷:牛贩客
这是古道上排第一个本钱大利润厚的买卖,老板多是黄岩口音。赶牛的汉子,则雇自留贤、八叠、石佛洋等地。沿途设有专供牛贩与牛群歇脚的“牛栈”,土墙旧院,夜闭门户,草料备足。留贤、坑头,几乎整村都是“草鞋之乡”。家家必备用以做草鞋的草鞋耙,以韧麻为经,金稻草为纬,制成耐磨轻巧的草鞋。留贤村有个特色,村戏棚正对着老爷殿。故有村谚云:“留贤戏棚对老爷,代代儿孙卖草鞋。”这草鞋,是脚担夫的护足之宝,更是黄牛跋涉的“蹄靴”。长途跋涉,牛蹄受不了石路的无情撞击,便会开裂。给牛穿上特制的“牛草鞋”——底部稻草编织,以麻绳捆扎于蹄上——方能护其行远。见过牛贩为牛穿鞋,畜生竟也温顺,抬蹄任人摆布。
牛群过八叠街时,蹄声沉闷而密集,草鞋之功,清晰可辨。场面浩大,五六赶牛人,驱赶着二三十头黄牛,一人管三五头,自成小队。牛贩居中,脖颈上挂满备用的牛草鞋,磨损即换。不见有骑在牛背上的贩子,人与牛,都在丈量同一条古道。
“温州有赶弗尽的牛,台州有杀弗尽的头。”这悲怆的谣谚道尽了两地命运:温州永嘉、乐清山多,多产黄牛;台州乱世,绿壳横行。二者在古道上诡异交汇。杭绍水乡平原,鲜少黄牛,水牛耕田,肉质粗粝。富庶之地,渴求温台山中健美的黄牛肉。一条利润与风险并存的贩牛链由此而生。北上的牛群络绎于途,也引来了绿壳垂涎的目光。时闻牛栈被劫,牛贩遭害的噩讯。也曾有荒诞一幕:夜雷雨中,几个绿壳企图打洞劫牛栈后院,未料雨水泡软了地基,小屋轰然坍塌,将一人活埋,余人作鸟兽散。年余后,屋主翻修,竟掘出森森白骨。
三、颤悠旅途:轿夫与蓝布轿
这是西乡相对体面的营生。沿溪大村,常备几顶村民自制的蓝布轿子待客。八叠村就曾有五顶常设。其用场甚广:送急病之人落城求医;客商往来赶路;雇不起花轿的农家娶亲;小脚妇人远赴天台进香。
我曾坐过一次。约莫六岁时,日寇逼近临海的消息传来,全家星散。我随母亲,坐上邻人的蓝布轿。轿身轻颤,吱呀作响,一路经包安、雨伞店、石佛洋,渡水至许岙,翻岭投奔后坑大姑家避难。姑家贫寒,却捧出珍藏的松花粉,做成金灿灿的麦糕待客。乍看以为是诱人的蛋饼,一口下去,粉屑呛喉,狼狈不堪。后来得知,日寇未至西乡,径取大田、亭旁,由海游港遁入大海。
那轿子,是门手艺。轿坤椅(特制竹椅)与轿杠分离。用前需“掰轿”:将竹椅分步绑牢在由两根长竹与两条短扁担共同构成、呈长方形的轿杠上。竹椅四周密布小孔,插入U形小苦竹竿,形成拱架,覆以蓝布帷幔。一张涂了桐油的轿席盖顶防雨。小被铺在椅面,设计精巧:前端可抽作搁脚板,椅背可适度放倒,可坐可卧。轿后还能绑一小箱,存放细软。大伯早年常坐蓝布轿往返天台经商,最远曾抵萧山闻堰访友。他笑言:“轿上一觉醒来,天台便到了。”
生意人常让货担先行,自己随后雇轿缓行,人货相随。贩牛的大老板,也多坐轿押阵。宦游人、商旅过客,皆汇此途。一到八叠街,需轿之声一出,轿夫们立时抛下手头活计,殷勤备至。一则百年行规,服务为上;二则扛轿收入远胜零工,乃村人一笔小小的“横财”,个个喜上眉梢。沿途客店对轿夫另有优待:无论坐轿人付费还是空轿回转,轿夫的食宿,皆按平价,这是古道上的温情规矩。
空轿回程,则拆作两件:轿坤椅与轿杠,由两轿夫分别肩扛,踏着归途的寂寞回家。
四、驿道余韵:石板与溪流
八叠街,这条驿道穿村而过的古老街巷。从下路廊而上,先是约五十米的街市,过小桥头,越大桥背(此桥宋时所建,今为省保),左折即上八叠岭。如今它已彻底沦为不起眼的村道。而我记忆中,店铺林立,行人如织,商旅喧腾,兴盛一时。历史深埋其下:村民挖地基,屡屡掘出两宋、元明各朝古钱,如时光遗落的鳞片,无声诉说着千年官路的繁华。
经过八叠的老驿道,是通往绍杭乃至京城(南京)的官道,数百年间堪称坦途。路面均宽六尺(大匠尺)以上,齐整异常——中间是四尺宽的青石板,两侧镶嵌鹅蛋大小的溪卵石。路面拱起,利于排水。这条石板官道与始丰溪如一对缠绵的伴侣,相依相伴。放眼望去,一溪清流,一路青痕,仿佛携手从天边蜿蜒而来,又携手隐入云雾缭绕的远山深处。
幼时记忆里,这路还有人维护。后来,渐渐荒疏。路人将石板撬起,修明坟、砌猪栏屋。临海古话“大路石板送人情”,其出典,大抵源于此。由台州府城来至天台去,有茶园岭、八叠岭、小石岭、百步岭四道小岭。为方便挑夫负重,岭路多以坡道为主。台阶费膝耗力,缓坡抬脚略低,肩上重荷,便在这细微的坡度里,省下了一丝喘息。
驿道在八叠岭上沉默延伸。风,依旧从江上来,吹过空荡荡的石鼓码头,拂过荒草丛生的古道,带着旧日挑夫的汗味、牛群的膻气、轿夫的号子、绿壳的戾气、石板缝里的铜锈气……也吹动着留贤村头尚未卖出的草鞋耙上,那几缕残留的稻草末梢。它们无声地盘旋,落在溪卵石上杠杆配资公司,落在被撬走石板后裸露的泥土里,落在这条曾经托起无数生计、如今已沉寂如深潭的古道上。
公牛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